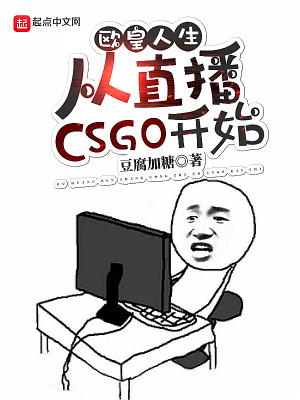下书网>毒酒一杯家万里 > 第45章 赵河明 不尊世上纲常不敬人间礼法(第3页)
第45章 赵河明 不尊世上纲常不敬人间礼法(第3页)
赵汉元咳了一声,抬眉问赵河明道:“你想起谁了?”
赵河明并没有隐瞒,反而张口重复了一遍赵汉元的话,“不尊世上纲常,不敬人间礼法……”而后续道:“这是陛下,赐给姑母的判词。”
此话一出,赵河明才终于明白,那阵萦绕在干风里的水汽到底来自哪里。
赵汉元长叹了一口气:“为父失言,你不必放在心上。”
“是。”
赵汉元不愿再言,侧身望向王灵官的神像,叹道:“你回府去吧。”
赵河明从蒲团上站起身,向赵汉元深揖,直身又道:“其实,也不必等开春,河道不通,陆路也未尝不可行,天机寺里的东西,能早一日运出梁京,就早一日。”
赵汉元沉默了一阵,方看向赵河明:“你在担心什么?”
赵河明沉默不答。
赵汉元撑地起起身,拢紧背上的大氅,走到赵河明面前。
“何礼儒虽死在天机寺的冰窖,但你已帮为父坐实了,他死于其妇刘氏之手。如今刘氏伏法天机寺火焚,天机寺内知情的僧众,大都已身死,剩下几个侥幸逃出的人,陛下也都赐了死罪,年后就要处死。何案至此,已经是个铁案。至于户部那三万金的亏空,就算日后查出来也是烂账一摊,往他何礼儒的那堆白骨上的一推就罢了,开春之前谁会想着,去挖天机寺那口冰窖。”
“父亲。”
赵河明打断赵汉元:“您教我的,这世上,就没有真正的铁案,即便天机寺已封禁,谁知道陛下何日起念重修……”
“兵部都在请发内藏,补郁州之兵,陛下如今,有这份闲钱吗?”
赵汉元说完,伸手扶赵河明直背,深看他的面容续道:“你的心思没有这么浅。河明,你跟父亲说一句实话,何礼儒的案子,玉霖到底知道多少。”
“她什么都不知道。”
赵河明直起身,目光侧向一旁,“就算她知道些什么,梁京地界上,她也做不了什么。”
“赵河明。”
赵汉元全名全姓地唤了他一声,赵河明眉头微蹙。只听赵汉元收起了原本平和的语调,沉声道: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,此事自古常有,对那个女子,你已经输过了,你不要太自信。”
此话刚说完,门外侍童忽通传道:“赵老,梁京来人了。”
赵河明闻话,亲手推开了殿门,只见门前站着赵家奴仆,“今儿午时,常在咱们阁老府上走动的一户部堂官来见老爷,穿着官服,行色匆匆地连拜帖都没有带,我们说,老爷观里清修去了,他也不肯离,只求要见老爷。”
赵汉元问道:“人在何处,引过来了吗?”
“引来了,在观外候着呢。”
“带进来。”
“是。”
家仆应声出去,赵汉元示意赵河明进来:“你先别走,跟我见一见这个人。”
赵河明自然认识,这个在其父门下走动的户部堂官,然而此人进来,根本来不及和赵河明见礼,只扑跪在王灵官的神像前,高喊了一声:“阁老啊,天机寺出事了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