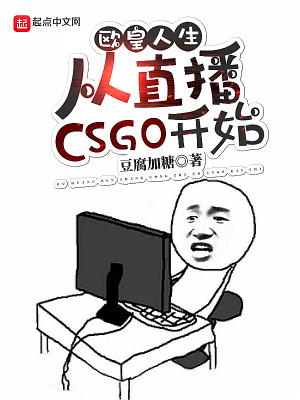下书网>毒酒一杯家万里 > 第104章 他可以 若玉霖这辈子想有一个男人(第2页)
第104章 他可以 若玉霖这辈子想有一个男人(第2页)
他已浑身湿透,冷清清地立在雨帘间,像一只白皙的幽鬼。
“我只是眼力不错,看出来人是她,她要绞我,我不得不缴械而已。”
韩渐总觉得这人说这话是有意在膈应些什么,但他又听不出究竟,只得“哦”了一声。
张药并没有在意韩渐的神情,他满口皆是诚得不能再诚的实话,再无一点心虚脸涨。
“至于贡院的案子,我至今不知全貌,今日来此,也是受她之令。”
说着,又望向了江惠云,肃声道:“不知夫人此来,是否也是听了她的话。”
江惠云稍稍偏伞,看了一眼张药的神情,不置可否。
张药续道:“我不知玉霖到底要做什么,更不知是否凶险,若她告明过夫人,请夫人赐教张药。”
江惠云撑着伞,踩着雨水走上前来,“你什么都不知道,就肯受她的令,一个人来这大理寺?”
“是。”
江惠云笑了一声:“你是镇抚司指挥使,是天子上差。你不要身家性命了,去听一个女子的话?”
“对。”
张药点了点头,他的确没有深沉心计和才思去与江惠云“周旋”,索性句句都实话,简短坦诚,引得江惠云笑开来,伞下抬眼,细致打量着他湿透的一身。
他从前正经时只穿飞鱼袍,平常办差为求便宜又只穿玄衫,俨然刀枪不入鬼神不近,此刻倒像是摘了盔卸去甲,素衣前来,可受一箭穿心。
“哼。”
江惠云哼笑一声,垂头收回目光,“我今日带韩渐过来,是为作证。当然,的确是玉霖求我带他过来的。”
“张药替玉霖谢过夫人。”
张药说罢,埋头深揖不起。
江惠云道:“你替她谢我?你是她的谁啊?”
这个问题似乎是说来诛心的,张药确实回答不上来,但他并不觉得难过。
管玉霖当他是谁呢?
若提男女之爱,皮骨相亲,又或者夫妻之情,耳鬓厮磨,他这个想死想了二十几年的人,绝不堪拥有,他也全然提不起兴趣。
可若玉霖想看看他的身子……
那他愿意。
他站在雨中,脑中一时涌起无数“虎狼之词”,偏心上灵台又清净无尘。
江惠云以为他吃了瘪,也不再纠缠,续上了之前的话道:“起初我并不想答应她。奈何这牵扯着几个年轻人的性命和前途,非我一人之事,所以还带韩渐来了。”
张药问道:“所以夫人,还是没有原谅玉霖?”
江惠云摇了摇头,“你这话问得真可笑,她要毁的是我的全族和我的夫君,我为什么要原谅她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