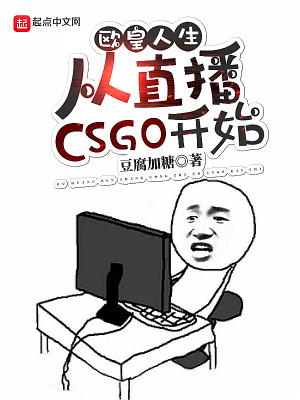下书网>大师兄说过 > 第186章 非草木二(第2页)
第186章 非草木二(第2页)
花农说道,“但我看这世道恐怕有些不太妙。”
他终于直起腰来,走回到摆着桌椅的树下。大小猫们很给他面子,椅子上的纷纷挪了开来,给他让出位置,只有一位趴在扶手上的仿佛觉得彼此并不相干,一动不动,只把耷拉下来的尾巴给收了上去。
院子主人坐进椅子,呼了口气。他面貌看起来并不老,但神色沧桑,一时让人难说他究竟多大年纪。那沾着泥土的手一招,一道水流从屋角的缸里跃来,他背过身,就着水流洗净了手,一边道:“凳子自己拿,就在棚子那边。”
孟君山老老实实地搬了凳子,回来在他面前坐下。对方不跟他客气,拣起竹箸吃了起来,又摸了摸那冰凉的酒壶:“说吧,这次又有什么麻烦事?”
“还真没有。”
孟君山道。
陆师叔道:“总不能是专程来延国看我的吧。衡文又怎么了吗?”
孟君山无奈一笑,对方就懂了:“门中事务,不好说是吧,你不必为难。”
说是这么说,过了一会,他还是嘟囔道:“衡文这搅风搅雨的架势,早该有人来管管了,看到你在这,我还能放下一点心。”
孟君山实在不知要如何说,他此行前来,并不一定能阻拦衡文的谋划,反而说不定要添上一把火。陆师叔觑见他眉间愁容,似有所觉,转开话头道:“掌门近来如何?——对了,刚经过凝波渡那一遭事,也好不到哪去吧。”
“师父并无大碍。”
孟君山道,“师叔隐居在此,也听到了仙门之间的传闻?”
“谁还能不知道啊。”
陆师叔唏嘘道,“真没想到会发生这等事。当年……”
他及时收住话头,将那不合时宜的感慨咽了回去。孟君山取出酒杯,为他满斟,陆师叔接了过来,奇道:“你不喝点?”
孟君山:“今日就算了。”
他们之间并无往来劝酒的俗套规矩,陆师叔也不在意,接过酒壶,自斟自饮起来。两人一时无言,三杯酒下去,陆师叔才道:“从凝波渡后,你见过谢玄华没有?”
“却是无缘见到。”
孟君山答道。
陆师叔细细打量他神色,皱眉道:“既没派你去与他会面,那我大概也知道掌门的态度了。”
孟君山默然。陆师叔道:“幸好他如今暂留王庭,否则他一回瑶山,必得令仙门众人难以安枕。只是可惜了你们两个的交情。”
“在我心中,我们仍旧是从前一样。”
孟君山低声道。
陆师叔道:“心中怎样想,又不作数。就是身不由己,你有苦衷,我能明白,他能明白——谁都明白了,难道就能说是丝毫未变?哪有这么容易。”
孟君山不禁苦笑。在此事上,他实则对所有人隐瞒了他两次见过阿花的关键,此事却是不好与师叔说的。虽然如此,他也不是对什么都问心无愧。
见他神色沉闷,陆师叔叹了口气,转而安慰道:“以后的事情谁也说不好,日后再看吧。至少眼下小心行事,你师父眼里可揉不得沙子。”
孟君山道:“师叔且放心。”
“哪里放心得起来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