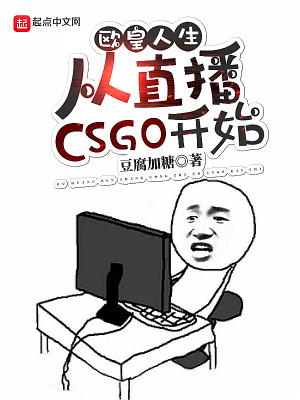下书网>鸳鸯床 > 第61章(第2页)
第61章(第2页)
东父:“这个人情欠的可就大了。”
东父还是感念祖上积德,能交上萧家这门亲戚的,要不然至今他跟东仕旻还在外流浪,无依无靠,没有钱财傍身,又以前锦衣玉食惯了,想给人做点伙计谋生都没有东家要。
他们都如此,就更不消说东月鸯跟妻子了,不祈求别的,只要能活下来就是天大的好事。
萧老夫人:“都是姻亲,我同惠娘还是结义姐妹,就算月鸯不曾嫁给鹤棠,你们还有仕旻就是他的世叔世母,还有弟弟,何须言谢。”
萧老夫人不想气氛太伤感,招呼众人都尽快坐下,东月鸯从东仕旻口中得知了许多不知道的消息,已经大概清楚他们经历了什么。
只是让她疑惑的是,“知不知道当初是谁抓了我们?”
她那个表哥牧信衡至今未得音讯。
东仕旻:“找到我们后,姐夫来信提到过,牧家的二表哥投了贼,就是他们那帮人干的,我和父亲其实在被捉住以后也察觉到他有问题,他还带上面具与我们交谈,试图蒙骗我们。”
但最终还是被东仕旻识破了,他人矮能注意到牧信衡掩藏在下巴处的疤痕,面具没挡完,叫他瞧见了,谁能预测最歹毒的贼人是身边的亲戚?
果然越熟的人越容易心怀鬼胎。
东月鸯好奇地问:“那他人呢,去哪里了?”
东仕旻摇头,“军队带兵压过来,剿匪,不出半日就破了金乌寨,他没杀我跟父亲,反倒把我们放了,让我们自生自灭,兴许也是自身难保逃难去了。”
眼下东家人最期望的就是回到以前稳定的日子,他们打算回去望天城,那里有东父创立十几年的家业,房子铺子奴仆也在,不知是否都被牧家给侵占了,总之该他们的还是要拿回来。
这种颠沛流离的经历这辈子都不想再尝试了。
东月鸯感同身受,她也是遇难过来的,摸了摸东仕旻的头安慰,“只要人没事就好,一切还有机会。仕旻,你和爹娘有没有受伤?打算在庸都郡待多久。”
东仕旻已经不像曾经那样天真了,可以说人虽小稚气却全退,“爹腿脚崴了,逃命时摔断了腿,后面接上了如今还能走路,就是瞧得出来。娘……没受什么伤,就是到了夜里容易受到惊吓,我们刚重逢的时候,她不爱见外人,看到什么都能吓到哭出来。”
他手伸出来,袖子拉上去,原本整齐的五指断了一根,东月鸯看到后心脏差点跳出来,握上去,“仕旻……怎么会这样?”
东仕旻平静的仿若不是一个孩子:“爹出去寻吃的,我一个人守在破庙里,遇到一个乞丐,他把我打晕了……醒来就发现他在把我……捧着吃。”
东月鸯闻言颤抖,东仕旻袖子滑落,原来他手腕上还散布着永久不能消散的齿印疤痕。
危难之际大人都难以生存,更何况稚儿呢,天下不是没有苦难,而是辉煌的辉煌,落魄的落魄,真验证了那句“路有冻死骨,朱门酒肉臭”。
东月鸯没想到年纪最小的弟弟比他们遇到的都要凶险如此之多,登时一口气没缓过来,她头晕晕地看着周围一切,一想到自己得救后日子过得太平,而亲人在另一头受苦受难,万念之间,愧疚亏欠涌上心头,难以呼吸。
“姐姐……”
东仕旻拉住她。
桌上其他人朝她看过来,萧老夫人担忧的眼神,东父东母麻木又关怀的脸,东月鸯迟缓地眨动双眼,天旋地转间一下晕了过去。
这一倒让萧老夫人彻底急了,“来人,快来人。”
东月鸯被扶起来,掐了掐她人中,还没苏醒,见此状下人赶紧去请大夫,剩余的将她背着送回了卧房。
“怎么会晕了,这是怎么回事?”